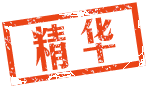|
|
本帖最后由 一舸烟雨 于 2011-6-5 16:54 编辑
诗意河洛风骨长
——读一舸烟雨的历史散文
一舸烟雨是洛阳偃师人。
他写了“诗意河洛 古韵三川”系列散文。有十多篇。
洛阳5000年的历史,风云变幻,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却只能惭愧地说:我了解得太少。我知道田横五百士的故事,却不知英雄就长眠在这里;知道碧血丹心的意思,却不知它就在洛阳上演着传奇;知道弦高退秦师的典故,却不知被秦顺手牵羊灭掉的滑国就是脚下的土地……
初读,我惊异于他深厚的文史积淀,引领我穿越历史的烟云,触摸这片土地的脉博,感受这块土地曾有的辉煌与悲凉。再读,却品出了它的厚重、诗意与风骨。
“若问古今兴废事,请君只看洛阳城。”这组作品和河洛文化一样典雅厚重。地上一个洛阳,地下一个洛阳,他感触着古都文化脉搏的生生不息;水逝云飞,物换星移,他从缑山夜月中看到了子晋哀怨的目光;小国寡民,刀光剑影,他从滑城烟雨中听到了无辜民众的伤痛;银条、牡丹石,河洛大鼓,牡丹,他吟唱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自豪……
他的散文又具有抒情的诗意美。写景优美细腻,景中寓情,情景交融,引用或化用古诗文句,能“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”,看似随意为之,却自有技巧。不着痕迹,自然贴切,表现出纯熟的文字技巧。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使文中诗意随处可遇:
何处无夜?何处无月?但缑山夜月总让你思接千古、梦回千年……《缑山夜月》
乱云飞渡,残阳如血。风过北邙,啸然有声……《何处吊田横》;
北魏一千三百寺,都在佛风禅韵中。《佛塔叩问》,
一阵山风吹过,红艳的野薇花晨星般闪烁摇曳在野草丛中,像点点化不开的惆怅……《薇绿首阳岑》
写史叙事如西洋油画般凝重浑厚,写景抒怀如中国写意画般灵动飘逸。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,一会儿是学者的严谨理性,一会儿是诗人的激情飞扬,一张一弛,变化多端,却又章法不乱,收放自如。
一舸烟雨擅长婉约诗意的表达,而且词汇量极大,用起来得心应手,但并非柔媚无风骨。风,是文章的生命力,是内在的、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。骨,是文章的表现力,是语言的准确、简练、明晰。风骨和诗意并不矛盾。像曹植就文才富艳,辞藻华丽,善用比喻,“骨气奇高、词采华茂”,建安风骨,就有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。曹植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,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历久弥远。一舸烟雨《开在牡丹里的洛阳》一文,就突出体现了文辞华丽与厚重大气的完美结合。
有无自己独立的风格与思想,是评价文章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。历史散文、文化散文要想体现风骨,必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感悟与理性的思考,仅向故纸堆里寻觅、闭门造车难成大气候。一舸烟雨时刻提醒着自己,文章越来越精彩。虽是一介书生,胸中却有浩然英雄气。他以深邃敏感的笔触穿透历史的迷霭,触摸人物的内心世界,直达精神内核,给予深刻的理解、叹惋、不平、敬佩。尤其令我激情澎湃、泪眼婆娑的是《何处吊田横》:
你以这样一种悲壮惨烈的方式,倒在了离古都不到30里的尸乡驿。尸乡是一道门槛,跨过去,是吉凶莫测的富贵,是壮志难酬的隐痛,是苟且偷生的耻辱,嗟夫,英雄末路,夫复何言!尸乡就是你不能渡过的乌江!于是你雄心不受北面辱,用巍巍首阳山,矗起你不屈的风骨!从海岛到洛阳,你死得不算决绝,但死得气贯长虹!
在《佛塔叩问》一文中,他发前人所未发,不但质疑佛塔高度,更关注的是对它历史意义的探究:
谁能告诉我,那高耸入云的巍峨,那雕梁画栋的华丽,那不可思议的精巧,是传播佛教教化世人威慑少数民族的治国安邦之策?还是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的劳民伤财之举?
在《烟雨滑城》中,他凭吊烟雨台,哀民生之多艰:
滑城烟雨呢——你是用霏霏细雨稀释着历史的伤痛?还是涤去岁月的尘埃让人铭记那久远的过去?抑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寄托了后人对沧桑历史的凭吊和纪念?
这组散文,充盈着闪光的智慧,蕴涵着深刻的思考,饱蘸着浓烈的感情,凝结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。
烟雨说他上高中时有两门第一:语文第一,数学倒数第一,因此被拒在大学门外。当了十几年的编外民师,工资微薄。后来又从事了种种工作。再苦再难,却从未放弃过对文学的痴迷。
一个目标笃定的人,一个怀抱梦想的人,自然会像他笔下的玄奘一样,在艰难的跋涉中,哪怕艰苦卓绝,也要虔诚、坚定、自信、从容地向前,永不止步。
从这组文章的多次修改中,我相信:他一直在写作中思考,在思考中修改,在修改中提高,在提高中探索出一条路,渐入云端,让我仰望。
我常想,凡尘俗世中的作者,于无人处又是怎样一种孤洁的情怀?
在生活中,我们该怎样保留一片心灵的净土,保鲜一份执著的梦想?
剪一窗月色,品一杯清茶,走近一舸烟雨,走近《诗意河洛 古韵三川》,走近洛阳,听历史的足音在心中激起的回响……
这是文苑才女村姑近日发在河洛文苑的一篇评论。
|
评分
-
查看全部评分
|